魏邦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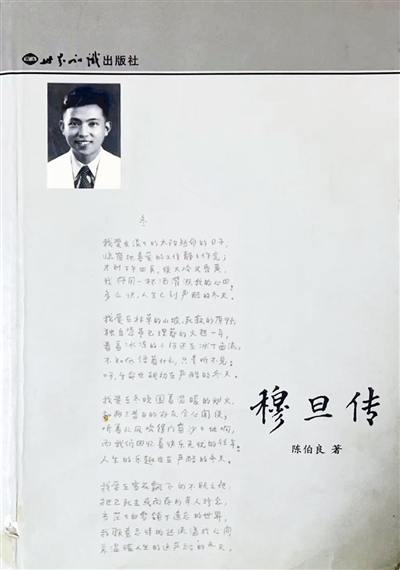
陈伯良著《穆旦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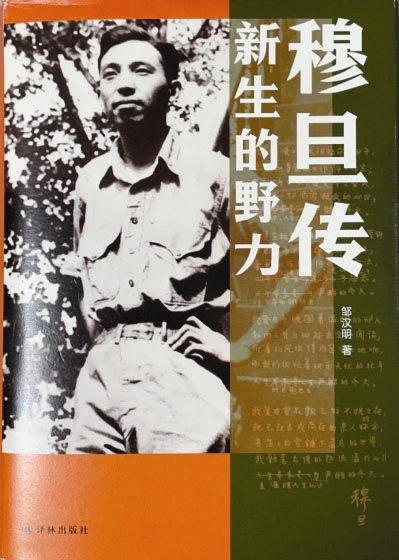
邹汉明著《穆旦传:新生的野力》,译林出版社2025年出版

1935年至1937年在清华大学期间的穆旦
今年全国高考语文一卷作文题引用了穆旦《赞美》中的诗句:“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穆旦,这个对很多人都显得陌生的名字,瞬间刷屏。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读西南联大期间,二十出头的穆旦就创作出大量精美诗篇,被誉为“西南联大三杰”之一,另外两位是郑敏和杜运燮。二十三岁的他就写出当时广为流传且至今光芒四射的《赞美》,他由此成为当时中国诗坛最亮眼的一颗星。1949年,他追随恋人赴美留学,就读于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
1952年,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后与妻子决定回国,因美国政府的阻挠,穆旦夫妇直到1953年才得以重回祖国,任教于南开大学。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穆旦专注于外国诗歌的翻译。当人们在他高贵典雅、富丽堂皇的译文中流连忘返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译者查良铮就是当年的穆旦。昔日激情飞扬、才气逼人的杰出诗人,已然成为安静内敛、字斟句酌的译界名家。
一
——南开中学和清华大学的校园刊物是诗人成长的“摇篮”
1918年4月5日,穆旦出生于天津老城内恒德里3号,本名查良铮,祖籍为浙江海宁县。
1929年9月,穆旦考入赫赫有名的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有自己的校园刊物《南开高中学生》。这个刊物为热爱文学的穆旦提供了最早的发表园地。
1933年12月16日,穆旦创作了短文《梦》,发表于1934年1月5日出版的《南开高中学生》,这是他首次以“穆旦”笔名发表作品。
穆旦十六岁那年创作的诗歌《流浪人》,是迄今发现的穆旦最早的一首诗,发表于1934年5月4日的《南开高中学生》上。此后,穆旦在《南开高中学生》陆续发表诗作《神秘》《两个世界》《夏夜》《一个老木匠》《前夕》《冬夜》等。有学者评论:“从《流浪人》到《神秘》《两个世界》,技艺的进展不是一点点,简直是突飞猛进。”(邹汉明著《穆旦传:新生的野力》)
穆旦高中同学周珏良曾任《南开高中学生》干事长兼总编辑,因编刊需要,常向穆旦催稿,晚年的他曾提及此事:“当时南开高中学生有一个刊物,叫《南开高中学生》,一九三四年我和穆旦都在高中二年级时我当选为主编。每一两个月出一期。当时他是写稿人的两大台柱之一,主要是写诗,也写些散文。每到集稿时,篇幅不够,我总是找他救急,而他也总是热心帮忙,如期拿出稿子来。”(李方《穆旦(查良铮)年谱》)
在南开高中毕业前的一年半时间,穆旦在《南开高中学生》这个学生刊物发表了四篇文章和八首诗。
1935年,穆旦高中毕业,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同时被三所大学录取。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就读外文系。
清华大学当时有校园刊物《清华副刊》和《清华周刊》,穆旦诗作《我们肃立,向国旗致敬》《更夫》均发表于校园刊物。此外,穆旦还发表了两篇散文《山道上的夜——九月十日记游》《生活的一页》。
在清华读书时,穆旦爱上燕京大学一位叫万卫芳的女生,恋爱中的穆旦写了一首爱情诗《玫瑰的故事》,发表于《清华周刊》第四十五卷第十二期。这首诗是根据一篇英文小品《玫瑰》改写的。诗中诗句预示这场恋爱将以失败而告终:
她年轻,美丽,有如春天的鸟,
她黄莺般的喉咙会给我歌唱,
我常常去找她,把马儿骑得飞快,
越过草坪,穿出小桥,又抛下寂寞的墓场。
可是那女郎待我并不怎样仁慈,
她要故意让我等,啊,从日出到日中!
在她的园子里我只有急躁地徘徊,
激动的心中充满了热情和期待。
(邹汉明著《穆旦传:新生的野力》)
后来,万卫芳服从家长安排,嫁给了一位富家子弟。
二
——从西南联大文艺社升起的一颗耀眼明星
北平沦陷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徙到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
临大设备简陋,条件艰苦,但师资力量雄厚,其中,对穆旦影响最大的当属英籍教师燕卜荪。
同学周珏良曾谈及燕卜荪对学生们的教诲。他说,因燕卜荪的影响“我们接触到现代派的诗人如叶芝、艾略特、奥登乃至更年轻的狄兰·托马斯等人的作品和近代史的文论。……我们从燕卜荪先生处借到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爱克斯尔的城堡》和艾略特的文集《圣木》(The Sacred Wood),才知道什么叫现代派,大开眼界,时常一起讨论”(周珏良:《“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学习英语五十年》)。
穆旦就读的外文系属于文学院,临大文学院设在南岳圣经学院分院。穆旦在南岳创作的《野兽》后来排在穆旦第一部诗集《探险队》之首。当时南岳有多次诗歌活动,如诗歌朗诵会、出诗歌墙报等。北京大学外文系38级王般主编了两期墙报,《野兽》即刊登在其中一期上。王圣思称赞这首诗为“一曲生命不息的野性赞歌”,赵瑞蕻认为,这是穆旦最好的作品之一。
战火很快蔓延到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迁徙,远赴云南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到昆明后,因校舍不够,文学院和法学院暂时设在比较偏远的蒙自小城。
在蒙自,穆旦加入了南湖诗社。1938年,蒙自分校文学院部分学生,在闻一多、朱自清指导下成立南湖诗社,取名“南湖”,因为蒙自有一个美丽的南湖。在南湖诗社成立之前,发起人刘兆吉征求穆旦的意见:“他不只同意,而且热情地和我握手,脸笑得那么甜,眼睛睁得那么亮,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以后凡大会小会,他都按时参加,而且积极投稿。……每次出刊,穆旦都带头交稿,有时也协助张贴等繁琐工作……我和向长清有时也请他帮忙审稿……我们往往都听取他的意见。”(刘兆吉:《穆旦其人其诗》)
参加诗社的同学采用壁报的形式投稿,就是把稿件贴在大牛皮纸上,张贴于校舍墙壁上。穆旦每次都积极投稿。
南湖诗社在蒙自出了四期诗刊。刘兆吉回忆:“南湖诗社,应当肯定是西南联大师生最先组建的文学社团,穆旦对南湖诗社是有贡献的。”穆旦诗作《我看》和《园》均发表于南湖诗社的壁报上,其中,《我看》写的是南湖及其周边的风景,作者就是在南湖公园写出了这首诗。赵瑞蕻认为这首诗是“‘五四’以来中国新诗中的精品”(赵瑞蕻《南岳山中,蒙自湖畔》);《园》则是穆旦向蒙自告别的诗。两首诗显示出诗人早期诗作的特色,是诗人成长道路上的重要作品。
文学院从蒙自回到昆明后,因昆明位于高原,南湖诗社便改为高原文艺社。高原文艺社是西南联大第二个文学社团,其成员基本以原南湖诗社成员为主体,吸收了一批新成员。因刘兆吉升入大四,负责人改由向长清担任。南湖诗社,只写诗,高原文艺社成员除了诗歌创作还包括散文写作,办《高原》杂志,两周出刊一次,依旧以壁报形式出刊。穆旦在回忆中说:“社中活动为在校中出壁报,……出过一次副刊,并经常茶会聊天。”(穆旦档案《历史思想自传》)作为高原文艺社成员,穆旦发表了《合唱二章》《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等诗作。有学者评论穆旦这几首诗“正在进行多种诗歌的探索,其诗风也在探索中发生着变化”“反映出穆旦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变”。
高原文艺社后来又演变成南荒文艺社,发起人是萧乾。萧乾当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他发起成立南荒文艺社是为文艺副刊培养一支稳定的作者队伍。包括穆旦在内的高原文艺社的文艺骨干基本都加入了南荒文艺社。1939年5月,南荒文艺社在翠湖公园里的海心亭举行成立大会。要求每位社员向社里交作品,社里推荐发表,发表时文末注明“南荒社”字样,稿费归社里,作为活动基金。穆旦名作《从空虚到充实》就以南荒社名义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
穆旦是南荒文艺社唯一写诗歌的成员。这段时间他创作的《劝友人》《从空虚到充实》《童年》《祭》《蛇的诱惑》《玫瑰之歌》《漫漫长夜》《在旷野上》迄今都没有失去其生命力。《防空洞里的抒情诗》是穆旦写于高原文艺社时期的作品,但发表于1939年12月18日的香港《大公报·文艺》,诗后注明“南荒社”。有学者评论:“这首诗对于穆旦的意义,在于奠定了他在南荒社时期的诗歌基调:内容上的自我解剖,形式上的散文化。”
对于加入南荒文艺社后穆旦所创作的作品,评论家评价如下:“穆旦在南荒社时期仍处于诗歌创作的转变与发展之中。南湖诗社时期,穆旦以浪漫主义为主调,高原文艺社时期开始向现代主义转变,南荒文艺社时期基本实现了转变。这时,穆旦的诗作全是现代主义的,虽然表现出了深刻的锐气,有了一些力作,但十分成熟的作品还没有出现。”《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
三
——半数诗歌创作于冬青文艺社时期
随着一些成员毕业离开,南荒文艺社衰落下去,而另一个文学社团——冬青文艺社应运而生,取而代之。在西南联大文艺社团中,冬青文艺社历史最久、影响最大。冬青文艺社还是以壁报的方式发表社员作品,另外,还“出版”手抄杂志,就是社员们用同一种稿纸抄写文章或诗歌,装订成册,放在阅览室中供人翻阅。这种手抄杂志分为四类:《冬青小说抄》《冬青诗抄》《冬青散文抄》《冬青文抄》。
1941年初,冬青文艺社与《贵州日报》合作,出版副刊《革命军诗刊》。穆旦在《革命军诗刊》发表《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五月》《春》等水准极高的作品。
冬青文艺社曾筹办出版《冬青诗刊》,但愿望落空,却办成了另外两个杂志:《文聚》杂志、《中南文艺》副刊。《文聚》是一本纯文学刊物,是冬青文艺社社员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在冬青文艺社时期,穆旦创作迎来井喷,写了七八十首诗,占穆旦毕生创作诗歌的一半。他的代表作《赞美》《诗八首》均创作于这个时期。这段时间,他才情迸发,诗艺成熟,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使他跻身中国杰出诗人行列。
1940年11月,穆旦一口气写出三首著名作品:《还原作用》《我》《五月》。从这几首诗可看出欧美现代派诗歌对穆旦的熏陶影响,穆旦在《五月》中写道:
五月里来菜花香
布谷流连催人忙
万物滋长天明媚
浪子远游思家乡
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
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
它们能给我绝望后的快乐,
对着漆黑的枪口,你就会看见
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
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
无尽的阴谋;生产的痛楚的是你们的,
是你们教了我鲁迅的杂文。
……
(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正如穆旦好友王佐良说的那样,穆旦诗歌如《五月》等,“也显出燕卜荪所教的英国现代派诗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中国青年诗人的技巧和语言中去了”(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
在给朋友的信里,穆旦承认,包括以《还原作用》为代表的一些诗作,都不同程度受到外国现代派的影响。《还原作用》被闻一多选入《现代诗抄》,显示了它的影响力。穆旦自述,这首诗“表现旧社会中,年轻人如陷入泥坑中的猪,(而又自认为天鹅),必须忍住厌恶之感来谋生活,处处忍耐,把自己的理想都磨完了,由幻想是花园而变为一片荒原。这首诗是仿外国现代派而写的,其中没有‘风花雪月’,不用陈旧的形象或浪漫而模糊的意境来写它,而是用了‘非诗意的’词句写成诗。这种诗的难处,就是它没有现成的材料使用,每一首诗的思想,都得要作者去现找一种形象来表达;这样表达出的思想,比较新鲜而刺人”(《穆旦诗文集》)。诗人杜运燮认为,穆旦这段话无意间阐述了他对现代派诗的特点的理解,“对读者如何读穆旦的一些‘难懂’的诗很有帮助”(杜运燮《穆旦著译的背后》)。
1940年,穆旦毕业留校在外文系任助教。这一年联大决定在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处一个偏僻的县城叙永设一所分校,让大一新生在那里上课。穆旦作为大一英语老师也前往该地任教。
在叙永分校,《布谷》是学生最喜欢的壁报,取名“布谷”,“有催人耕耘,带来春的消息之意”,半月出刊一次,请了李广田任指导教师。《布谷》的撰稿人主体是学生,但也邀请了助教穆旦参加。穆旦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
叙永分校只维持了六个月,大一新生重回昆明,《布谷》随后停办,其成员大多并入了冬青文艺社。
四
——《赞美》出炉犹如“宝石出土”
1942年2月,穆旦又一连写出《春》《诗八首》《出发》。《春》发表于《贵州日报》副刊《革命军诗刊——冬青》,周珏良说:“《春》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被承认为一首好诗。”
冬青文艺社创办了《革命军诗刊——冬青》《文聚》《中南报·中南文艺》三个文学刊物,而穆旦在此期间也创作出《春》《出发》《森林之魅》堪称现代文学之巅的诗作。
《文聚》是冬青文艺社创办的刊物之一,它的作者基本都是冬青文艺社成员。1942年2月15日,《文聚》创刊号问世,该期头版头条即穆旦的《赞美》,诗人林元评价道:“诗人对祖国和人民倾泻了海一样深沉的感情,用无数象征性的事物诉说一个民族走过的贫穷、灾难、耻辱的道路。颜色虽然暗淡,调子虽然沉郁,但主旋律却是昂扬的——诗人看到了人民‘溶进’了抗日洪流,激情地一再欢呼:‘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诗人的才华当时还被埋在泥土里,我们决定把《赞美》放在创刊号的‘头条’。宝石出土,便放出耀眼的光辉,当时就受到不少读者赞美。”(林元:《一枝四十年代文学之花——回忆昆明〈文聚〉杂志》)有读者评价:这首“悲壮滴血的六十行长诗《赞美》,歌唱民族深重的苦难和血泊中的再生”,承载着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的忧患和希望(陈伯良著:《穆旦传》)。还有评论家赞誉《赞美》说:“它宣告了一种新的美学观念的诞生,并把一种新的艺术风格推向成熟,因此,此诗在西南联大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也有人认为,《赞美》的发表是穆旦诗歌创作的一个转折点:“此前穆旦的诗以描写生命个体心灵的紧张剧烈著称的话,这之后穆旦的创作道路更宽广了。”(《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
而今年高考全国语文一卷作文题引用了穆旦《赞美》中名句,雄辩地证明了这首诗不朽的生命力。
穆旦后来又在《文聚》发表《诗八首》等代表作。
除了出版刊物,文聚社还出版文聚丛书,穆旦第一部诗集《探险队》就是“文聚丛书”的一种。
高中时,穆旦作为诗歌爱好者在《南开高中学生》初试啼声;读大学后,热爱创作的他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各种诗社的壁报上崭露头角。后期,联大社团与校外报刊合作,为包括穆旦在内的社员们提供更广阔更耀眼的版面。穆旦由一个青涩的文学爱好者成长为一个蜚声文坛的著名诗人,离不开校园社刊所提供的发表阵地。穆旦作为诗人茁壮成长,与文学社团热情洋溢的创作氛围,与社团成员之间的相互砥砺也有很大关联。
布谷催春,校园社刊如同“布谷”,一声声催出穆旦笔下一首首像春天一样美丽的诗篇。
(原文刊载于《今晚报》2025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