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钥匙奖章的故事】
◆廖世承在布朗大学读书的时候,中国留学生重读一两次并不鲜见,连美国本土学生,十之三四不合格也不足为怪,而廖世承凭借自己的刻苦奋进,在四年内读完六年课程,还被布朗大学荣誉学会吸收为荣誉会员,荣获金钥匙奖章。有次外出,有善良的路人见他是中国穷学生,有施舍之意,廖世承示之以“金钥匙”奖章,路人收回怜悯之情,向他致以敬意。
【艰辛的山区办学之路】
◆蓝田在重冈复岭之间,办学条件艰辛,廖世承等人刚到时,校舍只有一间借用的民宅。他和师生在山坡上兴建了几幢土楼房作为新校舍;亲自挑着簸箕运土开沟,修建操场。当时学校每月所需经费须到百里外的新化县城银行领取,途中要在给过路人临时搭建的棚屋里借宿。山中土匪猖獗,学校取用的款项又大,一路充满风险,担心别人遭遇危险,廖世承每次都会亲往。
【学校要向民众敞开】
◆廖世承关注社会教育,一直倡导把学校的大门向社会敞开,他曾说,“关了门办学,不能称为‘学校’,只能称为‘修道院’……我们要把全国‘修道院’的门打开了,变成民众的学校。这一副重担子,又非师范学校来挑不可”。因此国立师范学院创办伊始,廖世承就鼓励学生创办民众学校,让附近失学青年儿童可以免费入学,同时还为周边几个省培训在职小学教师,为乡村教育服务。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若要简单描述廖世承,他欣赏的教育家风度:“能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如严父,如慈母,如光风霁月,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可能是最贴切的表述。
巴金、汪道涵、赵家璧……每一位都是值得独立成篇的名人甚至大师,在他们的求学记忆里,都有这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老校长。廖世承注重教育实践,著述并不多,他的身份更多是“校长”,办过两所全国闻名的中学,在战时赴湖南创办国立师范学院,一生都行走在他最感兴趣的、带给他“活力”“愉快”“生命”的教育事业上。
【学术档案】
廖世承(1892—1970),字茂如,教育家。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就学于清华学校高等科,留学美国布朗大学。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后更名东南大学)教授、兼附中主任。1927年赴上海光华大学任副校长兼附中主任。抗日战争期间,在湖南蓝田任国立师范学院院长。1947年回上海,任光华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校长。1951年起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第一师范学院院长、上海师范学院院长等职。注重教育实验和教育科学发展,积极提倡和推行智力测验。对中学教育有深入研究。著有《教育心理学》《测验概要》《教育测验和统计》《中国职业教育问题》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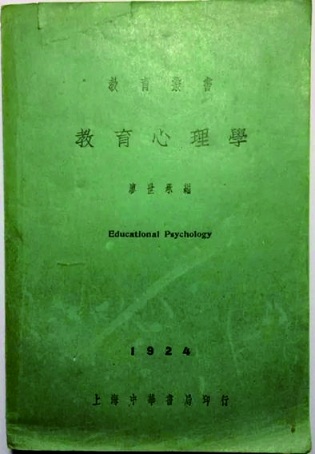
廖世承代表作一览 《教育心理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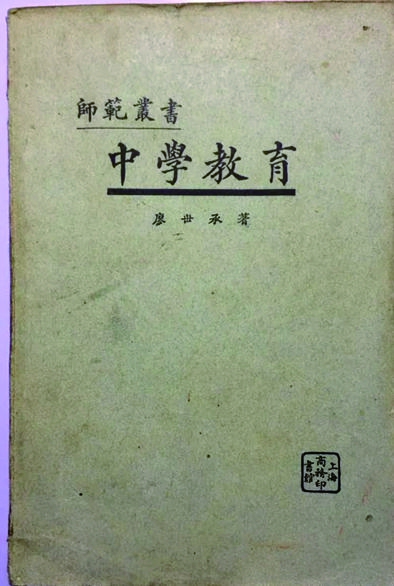
《中学教育》
如果没有旁人的提示、后来人的纪念,廖有盼并不清楚言语不多的爷爷廖世承在教育领域曾有着如此卓著的成绩:他专研教育心理学,把科学方法应用于中国的教育领域,他倡导的教育实验运动,推动了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科学化,许多教育教学研究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奠基意义。廖世承终身的事业就是办教育,人生中使用最多的社会身份就是“校长”——中学校长、大学校长。他是中等教育专家,更创师范学院独立办理之先河,赴湖南创办国立师范学院,后来也是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首任院长。从他执掌的学校走出来的知名人士不胜枚举:巴金、汪道涵、赵家璧……
“教育是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有力工具”
1892年,廖世承出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的文化世家,父亲是清末“桐城派”成员、圣约翰大学的国文教授廖寿图。在廖世承的记忆里“父亲博览群书,记性很好,掌故又熟悉,每逢晚膳时,总喜欢把历史上的事实及有趣味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廖世承听得眉飞色舞,有时慷慨激昂,“这对于我性情上的陶冶,确有不少影响”。廖世承6岁入伯父家开的私塾,13岁进了舅父家设立的中城两等学堂,加上记忆力好,读书不费力,无论家庭背景还是个人天赋,读书之路都是顺理成章的。幼年的廖世承喜欢看小说,尤其是武侠小说,时常使枪弄棒,仿效拳师力士的行为。而后进了南洋公学,性情大变,喜看明儒学案,对国文兴趣浓厚,也有作文的天赋,正课之外进了国文补习班,从乙班一路升到校长唐文治亲自授课的特班。南洋公学一段,廖世承渐渐对学问、时事产生了兴趣。毕业后,有亲戚推荐他去湖南教书,家境虽清寒,但廖世承不愿学业半途而废,取得父亲同意后入清华学校读书,也是这一决定使得廖世承人生之路的可能性从一个普通教师转向了影响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教育家。
清华三年读毕,廖世承获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家族希望他学银行、工程这些看得见“金饭碗”的专业。清华学校当时的校长周诒春则希望他从发展民族教育的需要出发重新考虑专业。看着满目疮痍的国家,廖世承不顾家族反对改选了在当时“最没出息”、只能当穷教师的教育学,如他后来所说“教育是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有力工具”,他选择了教育作为救国的工具。
廖世承留学期间,因为读书好,得到许多教授青眼相看,但中国学生的身份也让他受过不少刺激,对此他常想“回国以后,对于国人,任何意气可以消释,惟对于侮辱我的东西各国,定须争一口气”。他的拳拳之心,一开始是学业上的不肯落于人后,在布朗大学,廖世承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在四年内读完六年课程,成为该校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亚洲学生,如今布朗大学的网页上还保留着这条关于“第一”的记录。回国后,爱国之心化作教育的信念:“中国人要办好自己的学校——光我中华!”因为这份信念,他在东南大学附中停摆后,拒绝了多份工作上的邀约,其中就包括上海工部局给出的“华人教育处处长”这类高薪职位,而是选择了创立不久的光华大学——光华大学有着爱国的血统,“五卅”惨案发生后,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师生不满校方做法,脱离圣约翰大学成立了这所学校。廖世承任光华附中主任的时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意图大举进犯我国领土的时期。学校每星期的周会,廖世承总会向全体师生谈形势,谈救亡图存之道,并要求同学们面对这样的形势,决定自己准备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学生记得,高一的时候,廖校长给学生们读的是《中国近百年史》,而不再从三皇五帝读起。
“中国土地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众多,政治如此黑暗,人心如此陷落,专凭教育救国,哪里救得过来。但是除去教育,又向哪里去找。”廖世承对国情有着清醒的认识,他选择在教育领域深耕,冀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这个国家带来一些改变。
“凡教育上之新学说和新设施,皆采择而实验之”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杜成宪看来,廖世承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科学化的发展——他身上的科学特征尤其明显。“廖世承先生所学的教育心理学更偏于理科,其中涉及的测量、测验及实验属于工具类基础性学科,这与同时代偏文的许多教育学者是截然不同的。”
廖世承回国后,自然也将4年间掌握的科学方法带回了国内,他积极倡导和推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是20世纪20年代在我国推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的杰出代表。他参与创办南京高师心理实验室,这是我国最早的心理实验室之一;与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合作编制的测验法,连美国测验专家麦柯尔也不得不承认,至少与美国的水平相当,有许多比美国还优。
“教育测验刚引入国内,意义是积极的,它可以用来测量学生的学力,以科学的方法认识人在认知水平上的差异,进而因材施教,为当时的学制改革,特别是实行分科制和选科制时进行能力分组奠定了基础。”杜成宪谈及的正是廖世承推行教育测验的初衷:办学者不察学生的个性差异,不去研究适应个性的方法,把“智者、愚者、程度高者、低者、知识丰富者、缺乏者,强纳之于一炉”,必会使教授困难,效率低下,程度下降,天才埋没。
除了智力测验,廖世承的测验同样重视对性格和品性等非智力因素的测量。他认为,智力对人类有重要意义,但一个人的成功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智力。高智力的人在生活中可能没有成功,因为他们缺少特定的、对成功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素质。而平常智力的人也可能取得突出的成就——如果他们有良好的道德意识。在教育学者张民选看来,廖世承先生把中国的非智力因素的研究提前了60年。
五四运动后,西方的各种思潮、方法大量涌入,冲击着国内传统的教育框架。尽管接受过西方教育,但廖世承并不迷信西学,他多年留学所得也不是直接照搬到国内的课堂上——他有着理科生的视角,坚持先做实验,用事实说话,如他所说“从事教育的人当注意实地研究,不应作趋势论调。实验有效,然后再谋推行”。当时,美国刚刚兴起的教学方式道尔顿制传入国内,众多学校积极效仿,甚至形成了不做就是落后的风气。廖世承想到的是,设置两个平行班,一个采用道尔顿制教学,一个延续传统的班级制,作对照研究。道尔顿制鼓励学生自学,老师辅助,但实验结果显示,这种教学方式虽有利于个人的能力发展,但弊端也很明显,在基础知识的普及上不如传统的授课方式,对于当时的中国并不适合。廖世承的实验结果,给了盲目追求西方教学理念的人们一个清醒的认识,更唤起了教育界的实验兴趣,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科学化的步伐。值得一提的是,《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发表多年后,日本、苏联等国也相继否定了道尔顿制。
廖世承“凡教育上之新学说和新设施,皆采择而实验之”,从课程教材编制到学校管理,都以实验的方式给出最佳答案,他接手的两所中学可以迅速成为全国中等学校的翘楚,与此不无关系。1924年,廖世承基于各种教育实验、测验实践以及国内外最新的教育心理学研究,编著出版《教育心理学》,这是我国最早的高师教科书,而廖世承也被学界公认为我国教育心理学科创始人。
“他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在于如蔡元培和陶行知等人那样构建了一个宏观的教育理论体系,而在于他立足于教育实践,在一个个具体的实践需求迫切的教育课题中提出了自己的独到主张,最终达到了理论创新的效果”,对于廖世承在教育领域的学术贡献,张民选曾这样概括。
参与学制改革,培养学生品性,他是一代中等教育权威
廖世承非常看重中学教育。他倡导教育救国,认为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又以青少年教育为国家兴亡的首位要素,“今天的青少年就是未来的国民。他们的素质如何,是忍辱负重,殚精竭虑,积极建设,还是为个人名利地位?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社会的进退、民族的隆替”。而在他眼中,中学教育是整个教育最基础、最活跃、最生动的阶段,这一阶段做好了,为后面的教育,为人的成长都打好了基础。因此,他曾顶着众人的不解眼光,辞去了社会地位更高、能带来更多声望的大学副校长一职,专心做一个附中的主任。他说:“教育是精神事业,一分精神,一分效果。不论办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精神本无二致。”
廖世承是中等教育权威,就学制改革、课程改革、教法改革都有自己的见解,并积极参与其中。留学归来,廖世承就参与了学制改革的讨论:民国初年的教育学制,小学长达十年,中学不分等级,改革学制已成教育界共识,尤其针对中学学制如何设置,教育界众说纷纭。教育界泰斗蔡元培提倡“四二制”,认为初中四年涵盖整个中等教育,高中两年作为大学预科,最符合世界潮流。而初出茅庐的廖世承却大胆地提出了不同意见:“三三制”符合青少年个性发展需求、适应时代潮流,既可使“各段教育相衔接”,又可“顾全升学与职业两种”,从国情上来讲,加上中学之前的小学六年,“六三三”学制更为经济,更贴近学生家庭的承受力,因此更为合适。通过东大附中的实践和对国外学制的研究,以及在济南、武汉等地的实地调查,廖世承进一步证明己论。“六三三”学制推行后,中途退学的学生大大减少,契合了教育普及的国情需求。
廖世承非常清楚中等教育的目的“在培植社会基层事业之干部人才”,应以培育生产技能,发扬自治能力为宗旨。中等教育的对象是“正在发育变化之青年”,因此要培养他们多方面的兴趣,发挥他们潜在的能力。而办教育的人“当随处替学生设想,减少他们时间和精神的浪费”。廖世承看到当时的学制课程大都抄自西洋各国,不仅疑问“这种课程,于我们现时的生活,有几多关系?于儿童将来的生活,有几多关系”,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众学校至少有一部分的精神财力因为课程编制不适当而浪费。因此他提出用科学的方法,根据现时社会需要、参照社会进化的历程改造课程。在中学课程改革中,廖世承提出三条指导思想:首先,鉴别个性,加强教育效率,减少中途辍学人数;其次,采用分科选科制,变更完全预备升学的目的,使学生有一部分自由选择的机会;再者,破除学年制,采用能力分组方法,以学科为单位升班。这些改革克服了传统班级授课制和学年制的弊端。对于教学上的弊端,他也是直言不讳:“现在的教师,病在教学科,不教学生;教整个的班级,不教张某李某单独的个人;教数目,不教千变万化的活人。”廖世承认为,教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学,而要学生学,必须鼓励学生、引导学生,使学生处于学习的情景之下。
相对于知识的灌输,廖世承认为学校教育应更重人格的培养,认为学校专尽了“教”的功夫,不尽“育”的责任;专供知识,而不问应用知识的人的人格如何,不仅有许多流弊,而且是十分危险的事情。“现代的国民,有体力,有智慧还嫌不够,必须要有健全的人格。要知人格健全,不但使国家、社会蒙其益,个人也有无穷的乐趣,一个民族的强盛与该民族的民族意识和修养素质是密切相关的。对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态度,也是人格的表现。”廖世承注重德育,也注重体育,有学生忆及当年,曾感慨:虽然当时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尚未明确提出,但廖先生领导的附中在这方面已努力以赴了。
办学从来都不是易事,廖世承却乐在其中:他认为中学校长就是“一天一天造就青年的人才——他是社会的先导,社会进化的领袖,负重大责任的一个人。他的物质上报酬,虽是有限,精神上的快乐,却是很少人能比得上他”。
创师范学院独立办理之先河,为教育培养后继人才
有人说,中国高等师范教育体系上,应该庄重地镌刻上廖世承的名字。
办了十几年中学,廖世承深感师资对学校的重要,他把教员看作学校命脉,曾说“一个学校的最后成功,就靠教师。无论宗旨怎样明定,课程怎样有系统,训育怎样研究有素,校风怎样良善,要是教师不得人,成功还没有把握”。他认定“教育方面最重要的,当然是师范教育”,因此对中国师范教育也作了悉心研究,提出了师范学院附设于大学利少弊多,应以独立设置为原则,才能培养良好的师资,使中小学有稳定的、有质量的师资来源。
抗日战争爆发后,廖世承付诸心力的光华附中被夷为平地,此时教育部以中等教育司司长职位相邀,廖世承没有接受,却接受了教育部另一个聘请——赴湖南筹建国立师范学院。相比教育司长这样的行政职位,到内地筹建学校是一桩异常辛苦甚至可能丢掉性命的差事。而对于廖世承来说,这为他实现独立创办师范学院的心愿,为国家、为民族培养教育人才提供了空间,因此他辞别妻儿和病榻上的老父,辗转多地,历经许多险境,到达湖南蓝田,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一座新的学校。炮火连天中,国立师范学院用时4个月建起来了,尽管看起来不甚气派,甚至有些简陋,但学校图书馆却是藏书丰富,甚至有明清刻本。师范学院当然要有好的师资,廖世承认为“师范学院之理想教授,须学识宏通,而且富有教学经验,具有教育热情”,凭借他在教育界的人脉和声望,他延揽了钱基博、钱锺书父子分别担任首位国文系主任和英文系主任,此外还有孟宪承、郭一岑、朱有光、高觉敷、刘佛年等,每一位都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留有名字。
廖世承十分强调教师的修养与素质,国立师范学院的缩写“国师”二字在他看来,可以拓展成另一个意思:国民的导师,因此他对师范生的培养要求非常高,他常说,“教师是非常专门的职业,不但要知识好,方法好,而且要有专业道德——有责任心、忍耐性、仁爱心、真诚、坦白、乐观、谦虚、公正诸美德”,高要求可见一斑。
教育救国是廖世承的本心,所以他格外关注社会教育,一直觉得知识阶级和民众的生活不能隔得太远,要把学校的大门向社会敞开,他曾说,“关了门办学,不能称为‘学校’,只能称为‘修道院’……我们要把全国‘修道院’的门打开,变成民众的学校。这一副重担子,又非师范学校来挑不可”。因此国师创办伊始,廖世承就鼓励学生创办民众学校,让附近失学青年儿童可以免费入学,同时还为周边几个省培训在职小学教师,为乡村教育服务。事实上,廖世承在光华任职时,就曾经组织和鼓励大中学同学筹办光华平民学校,为失学儿童提供免费读书的机会。
1940年代末,廖世承回到上海,先后任职于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1958年,上海师范学院成立,此前出任上海第一师范学院院长的廖世承接过了该校首任院长的重任。在新的岗位上,廖世承更加认识到师范教育应该与国家建设、发展紧密结合,热情地投入社会主义高等师范教育的实践。教室的后排,常会见到这位形容清矍的老人在听课,语言学家张斌在世时曾有过回忆,廖院长听过他主讲的课程之后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对作为教师的他从教育教学角度去建构课程很有启发,“廖先生考虑问题是站在高处的”。
回望50年教育生涯,廖世承也曾感慨,但从不后悔,他的目光一直望向教育的未来:“我是教育国地上一个垦荒者,从没有在一所学校内留得很长久的。倘使精力容许我的话,或许我今生再能开垦一片园地。”
(原文刊载于《文汇报》2020-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