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倘若我们不用什么“经典”之类词语去形容,说它是一块研究宋诗绕不开的学术界碑,应无疑义。可是,《宋诗选注》出版之时,却受到一些批评,有人甚至以当时流行的斗争观点对其严厉批判……一时间,很有些“山雨欲来”的感觉……

钱锺书

夏承焘
机缘巧合选注宋诗
1954年,钱锺书参与的翻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告一段落,回到原单位文学研究所。他多年来学的是外国文学,回国后在高校教授的也是本行,文学研究所成立,他自然是外国文学组成员,可这次回来,却被文研所长兼中国古代文学组长的郑振铎借调过来,工作是选注宋诗。“从此,一‘借’不复还,一‘调’不再动。”按钱锺书的说法,郑振铎让他干此事,也并非没有理由:“因为我曾蒙他的同乡前辈陈衍(石遗)先生等的过奖,(他)就有了一个印象,以为我喜欢宋诗。”(见港版《宋诗选注》序言《模糊的铜镜》)钱锺书涉猎广泛,与前辈谈谈古诗,给听者留下非常印象。
尽管此举非钱锺书所愿,后来其有诗云“碧海掣鲸闲此手,只教疏凿别清浑”,表示感叹,可对文学的喜欢,还是支持他把此项工作做好。此时,宋诗并没有人认真如《全唐诗》一般辑录,“选宋诗的人就没有这个便利,得去尽量翻看宋诗的总集、别集以至于类书、笔记、方志等等。而且宋人别集里的情形比唐人别集里的来得混乱,张冠李戴、挂此漏彼的事几乎是家常便饭……”(引自序言)幸亏钱锺书学养深厚,用了两年时间,搜辑辨认,遍读宋诗,在当时的时代气候下,独立完成了这部《宋诗选注》。

青年钱锺书与杨绛
时人对《宋诗选注》的批评
该书出版,从版权页可知,时间是1958年9月。由于其中的诗人小传及注释,精彩而别具韵味,《宋诗选注》得到许多内行学人(胡乔木、周扬、乔冠华,甚至胡适……)的称许。可当时报刊上,却出现了数篇态度严厉的批判文章。譬如1958年12月《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目,一下子刊发出两篇评论文章来。其中一文,篇幅大,且搁在最上位置,即胡念贻撰写的《评“宋诗选注序”》。此文不是全书的评论,而是针对钱锺书为此书写的序言而发。评论由一个转折句式开场:“钱先生在主观意图上也是想使在文章里面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也想使读者对宋诗的面貌有一些真正的了解。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限制了他,客观上不仅不可能达到这样一些目的,而且相去还很远。”
当时习惯先加一顶帽子。在对钱锺书序言做出种种分析(为节省篇幅,此处不作征引)之后,胡念贻结论:“钱先生掌握的材料是丰富的,他也想在文章里用一些新的观点,但是,新的观点敌不住他的旧的唯心主义观点……本来是爱好宋诗,而且选注宋诗,要向读者推荐的,结果却把它否定了,这是多么难于理解的事情,这就是钱先生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所弄出来的结果。”从此文可以看出,胡念贻本人对宋代诗作的基本情况是熟悉的,他的批评,大致还是在文学研究范围内进行的,虽然用了一些非文学的观点,间或穿插一些未必合适的“唯心”“唯物”词汇,但他指出钱锺书序言的某些问题,还并非无中生有,尽管不见得切中诗选者之深心。
《光明日报》发表胡念贻文章的同一版,刊出了黄肃秋的一篇《清除古典文学选本中的资产阶级观点》。对《宋诗选注》,作者开宗明义:“当我们仔细研读之后,发现这是目前古典文学选本中的一面白旗。”起首定性,先声夺人。“这是钱锺书先生《谈艺录》中观点的继续发挥,这是抽掉了作品思想内容专门从诗体演变上来选诗、解诗的形式主义表现。因此,我们非坚决地拔掉这面唯心主义的白旗……”总之,这篇文章用当时流行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从并非完全文学与学术探讨的角度进行了批判,从当下的文化语境下观照,难免有些偏颇。
这段话中的逻辑线索,太过跳跃。作者以为:在《宋诗选注》的序言、选目、注文中,“钱锺书先生把整个力量都花在对流派的叙述上,字法句法的探源索隐上去了。”“而对于十分重要的这些诗产生于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中,反映一个什么思想内容,却是避而不谈……”因此,作者就认定“钱锺书先生评选作品的标准是形式主义的,没有充分注意到作品的思想内容。”此文虽然举证不多,可结论却严重、严厉。这许多用辞,在当时不仅“唬人”,还完全可能给著述者带来真正的灾难。所以笔者对此文作者的写作方式深不以为然。
当时产生较大影响的批评文章,还有周汝昌的“读《宋诗选注》序”及刘敏如“评《宋诗选注》”两文。他们的文章,写作时也许并未见到前两文的发表,因此涉及内容及角度,多有重合。在此我们大致略去他们一致的地方,略略介绍他们文章其他部分。周汝昌在古典文学方面,除去《红楼梦》研究,还涉猎颇广,仅仅宋诗,就编选过《范成大诗选》《杨万里诗选》。他的文章,较他人的更有个人见解。譬如分析钱锺书序文三点,其中有二点这般认为:宋诗写作“作贼”的情况是有的,但也不能说凡是思路、手法、字样相近似了的就一定都是“盗案”。周汝昌认为:“作者由于创作上的种种条件的类似,如果思想感情相同,发生‘心同此理’的‘偶合’现象,应该是很自然的,古今中外,不乏其例。”
再,选注者(钱锺书)大力批判形式主义的流弊,固然是好的,可从全书看去,选注者一方面在理论上批判这种流弊,具体到作品,又以大量篇幅来注释它、突出它。选注者是以“掉书袋”的注释,来否定“掉书袋”的流弊。笔者以为,这两点周汝昌说得不无道理。谈艺术的部分,周汝昌能够津津有味,可后来涉及其他部分,他却似乎不能运用合切,故此不多征引。
另一篇言辞锐利,颇有批判力度的文章刊发在1958年第20期《读书》杂志上。作者刘敏如,文章题目“评《宋诗选注》”。此文作者开篇,抓住钱锺书序言中有关时代背景的问题,上纲甚高:“我们认为,一部断代诗选,应该在序言里系统地分析一下诗歌反映的历史情况,主要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下面的文字,都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的,我们不过多引述。后面,刘敏如概括说:“以上,说明作者在抽象的艺术标准和应酬式政治标准的幌子下面,偷运资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说明作者是割断文学和现实的联系,以便不受限制地任意雌黄,冲淡作品的现实性……正是目前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反映在文艺思想中的一股逆流。《宋诗选注》的选注者,就是这一类型。”
结论是:“这个选本,应该说仍是今天古典文学选本中的一面白旗,我们应该把它拔掉。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有责任把红旗插上去。”
为《宋诗选注》正名
引述略略多了一点,其实有必要。不如此,读者不能知晓《宋诗选注》此时面临的境况,也就不易见出夏承焘先生此时出手作文声援的分量。
这数篇文章,短时间集中发表,自然形成了相当影响。据资料,笔伐而外,还有口诛。譬如钱锺书所在的文学研究所,还为《宋诗选注》召开了多次批判会。当时钱因为参加“毛选”英译定稿工作,不能回所,会议成了缺席批判。文研所领导让钱夫人杨绛“代领转达”。杨绛在场,拿着本子记录着大家的批判发言,老老实实代钱锺书“挨批”。可如此集中而调门甚高的“笔伐”“口诛”,不多久便消停下来。据杨绛认可的《听杨绛谈往事》一书的说法,是因为日本汉学泰斗、宋诗研究专家吉川幸次郎对《宋诗选注》非常重视,推崇备至。另一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对此书也交口赞誉,甚至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一本从不同于前人的角度出发对宋诗进行全面观察的书。”“注释和简评特别出色,由于此书的出现,宋代文学史很多部分恐须改写”。由此,对钱锺书的批判旋即“偃旗息鼓”。
照当时情形看,仅仅日本学者高度评价,是否会对国内一场批判产生立即停止的效果,不见得,它可能是各方影响的一个较易表达的因素吧。
当时供职文学研究所的邓绍基回忆可以佐证:“这部被人称作‘宋诗学中的一部名著’的书一出版就受到好评,胡乔木同志和周扬同志都有称赞的话,后者是我亲聆的,记得是称赞书中多有见解,文字也漂亮。但好像也说了或许有过于追求文字技巧之嫌的话。”胡乔木和周扬,正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负责人,也是文学研究所的领导,他们均表示了对此书的赞许,从当时情形看,这应该也是使得对《宋诗选注》批判旋即“偃旗息鼓”的原因之一。
批判“偃旗息鼓”后,文学研究所负责人何其芳“一再请杨绛代向钱先生道歉”。此外,那几篇批判文章造成的效果,是否也得有说法?当时参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的刘世德回忆:“钱锺书先生出版了一个《宋诗选注》,在当时受到了批评。有人要‘拔白旗’,要拔钱锺书这面‘白旗’,认为《宋诗选注》是‘大毒草’。何其芳看了之后觉得很不公平。他觉得要找一位学者,重新评价《宋诗选注》。但是这位学者不要找北京的,要找外地的。找谁呢?他跟我商量了很久,最后确定找杭州大学的夏承焘。”
北京有如此多的古典文学研究学者,为何偏偏远道杭州去请夏承焘教授来写文章呢?首先,夏承焘是古诗词研究大家,再,他对《宋诗选注》颇有好感,对一股脑儿乱批并不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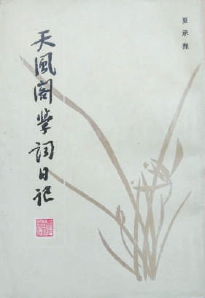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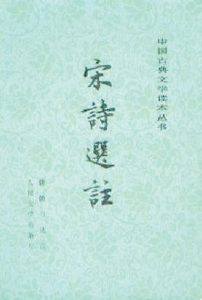
钱锺书《宋诗选注》
词学大家夏承焘伸援手
我们从夏承焘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可以读出这方面的记述。1959年1月7日:“午后看钱默存宋诗选注。近日报纸登此书批评文字数篇,予爱其诗评中材料多,此君信不易才。”(钱锺书字默存)除去称许著者为“不易才”,夏承焘还注意到了当时的批评文章。1月9日继续:“看宋诗选注。”此后出现了夏承焘被邀约写“平反”文章的机缘。当年4月,身为《文学评论》杂志编委的夏承焘,到北京参加编委会。该刊物编委会中,有何其芳、陈翔鹤、夏承焘、钱锺书等数十人。4月8日到京,在京期间也有提到《宋诗选注》的 地 方。4月 15日日记:“(王)任叔爱赏默存宋诗选注,谓论注文学书,应为作者留余地。”王任叔曾任驻印尼大使,此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曾以“巴人”笔名著有《文学论稿》,是文学通家。他“爱赏”此书,并以为讨论该书,应对作者“留余地”,应该是不满意一些人的批判调门儿太高吧?编委会开会期间,钱锺书与夏承焘见过面应该没有问题,想来也应该言及《宋诗选注》,可惜没有留下文字。可夏承焘对《宋诗选注》的看法,《文学评论》实际主持人的何其芳及其他编委有所耳闻,这才是远道约请的重要理由吧。
回到杭州,夏承焘就接到了钱锺书寄来诗作及一册《宋诗选注》。他的日记有言:“发钱锺书函,谢其寄来宋诗选注及诗,附去感近事一诗。”夏承焘给钱锺书的诗是《自京归杭得钱默存示诗感近事奉报一首》:
后生可爱不可畏,此语今闻足汗颜。
不信千编真覆瓿,安知九转定还丹。
是非易定且高枕,蕴藉相看有远山。
太息凤鸾满空阔,九州奇翼竟无还。
夏承焘此诗,定然是对钱锺书诗作的回复。诗作显然对《宋诗选注》充满信心,相信它不会“覆瓿”,事情当有变化(“九转定还丹”);且安慰钱锺书从远处看,“是非易定且高枕”。最末一句,夏承焘有注:“谓郑振铎。”郑振铎是文学研究所所长,不久前飞机失事殉难,他是赏识钱锺书,并安排钱选注《宋诗选注》的人。此句既怀念郑振铎,也含有此时少能有如郑振铎这样“慧眼”识钱锺书者的遗憾。
夏承焘对《宋诗选注》的肯定看法,钱锺书也很是感激。除去寄去作品(夏读过,显然已经有《宋诗选注》,钱锺书再寄一册,应是一种郑重且感激的表示)和诗作,夏5月22日日记:“钱默存寄来爱人杨绛所译法国萨勒日所著小说《吉尔·布拉斯》一厚册。”这仍是一种表达感激的方式吧。
日记6月11日云:“看钱默存旧作《中国诗与中国画》。”《中国诗与中国画》是钱锺书1949年前的名文,此时夏承焘阅读它,想来是为给钱锺书写“平反”文章做准备吧。接下来不长时间,北京方面有“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亲笔,也有刘世德以“文学遗产”栏目名义的函件不断催稿,可见当时编者,或许也反映了何其芳等相关人士对胡乔木、周扬表态后的焦虑心情。连续催索之下,夏承焘的文章也迅速动笔写成,7月9日:“命汝岳抄评宋诗选注文,午后寄出。”很快,这篇为《宋诗选注》“平反”的文字,于当年8月2日发表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目中。
夏承焘评《宋诗选注》
从这篇《如何评价〈宋诗选注〉》看去,夏承焘写文章的手法是很高明的。文章开首,他并不直接评价此书的内容:“选诗难,选宋诗更难。宋代诗人和诗作都不少,却不曾有一部完整的《全宋诗》,而宋人的题咏酬酢的作品特别多,散见于笔记、诗话乃至语录、类书里的,往往而是。”
那么,想要真正严谨选诗:“就必须认真地在蒐辑辨识上做一番功夫,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宋诗选注》成绩的重要方面,首先表现在选注者下的这一番“不容易”功夫。再往下说,“宋代诗多,诗论也多,论自己的主张,也论别人的得失。”所以,今天选宋诗“就必须自具一种手眼,把客观标准和主观好尚一致起来,不为前人所牵制……这就非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独至的见解不可。”
这就从多方面使人感受到选宋诗的极大难度。基于此,夏承焘才落笔到这部作品上:“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的出版,使我们耳目一新,得到很大的满足。”“这个选本,确实冲破了选宋诗的重重难关,无论在材料的资取上,甄选的标准上,作家的评骘上,都足以使读者认识到宋诗的面貌、它的时代反映和艺术表达……”
接下来夏承焘认为,一般的诗选,除了辨体、明例、综赅一个时代的文学成果,不外乎有三种性质:一,掇存;二,楷范;三,品藻。而“《宋诗选注》就其取材和对象言,乃是近于品藻的性质,而不纯是读本”。所以,评价它,这一点不可忽略。他进一步说:“好的选本实际上是选者的一种创造,好的选本是一个有机体,贯注在中间的是选者的识见、议论。”这几点,先前的几位评论者均未涉及,但却正是分辨、认识《宋诗选注》时应该特别留心之处。
在引证了几部传统诗选精心结撰评论文字后,夏承焘认为,《宋诗选注》继承了这个好的传统:“翻开这本书,最引人入胜的就是这些议论意趣洋溢的小序了。”跟古人比:“就更令人感到《选注》的作者对这八十位诗人的作品付出了多少涵泳体察的功夫。”在此,夏承焘确实是以“通家”的眼光,体察到选家的努力之处和独有的贡献所在,而这些价值和带有启示性的地方,其他几位论者没有见出或有意忽略了。
接下来说到宋诗的取材,夏承焘别异于其他批判者,认为“《宋诗选注》的甄录使读者感到一种积极的、向上的、健康的气氛,在作风上也较能清楚地看到不同作者的个性和创造性。”
夏承焘肯定了钱锺书选出的作品在精神层面的积极、向上、健康的一面。同时,他还认为,其中不少诗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宋代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鼓励了爱国主义和反抗精神。”这样也回应了先前批评者认为此书没有充分反映“民族矛盾”等看法。下面,夏承焘没有沿着此思路延续,笔锋一转,他认为宋诗的形式主义是严重的,所以钱锺书对有形式主义特点的诗人,甚至大诗人也保持警惕,选诗十分严谨。
并且,《宋诗选注》也不忽视人们历来喜欢的苏轼、王安石、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名家的作品,对于其他人批评该书选入的描写个人生活意境、流连光景的作品,夏承焘则认为:“这些诗篇有较高艺术成就,基调也是高朗健康的……我们应该知道它,并且欣赏它。”这就轻轻且自然地拨荡开诗作只是表现生活中“斗争”一面的偏颇。
说了此书很多好处,也或明显或含蓄回应了前面批判文章的看法后,夏承焘也谈到了《宋诗选注》可见的问题:“作者虽不赞成那种‘无一字无来历’的见解,但在注里有时也采取了委曲寻究,旁通发明的办法,更有时不免有过于求备之处。”当然,对于古典诗歌选注本,这无论如何是可原谅的地方。最后,夏承焘结论是:“《宋诗选注》对我们说来也许是更切近,更容易领受些。”总括起来看:“古今来大约很少有厘然允当于万千读者之心而全没有缺点的选本吧。如果不是阿其所好,我觉得钱先生的这本《宋诗选注》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夏承焘文章虽然说不上定论,但《宋诗选注》的好处及其特别着力之处,却较为公允地阐述清楚了。在当时,从严厉批判到指出优长,此文显示了某种程度的文艺回归,当然,后面的政治表态成分,更不可忽视。这之后,对于《宋诗选注》的严苛批评文字,再不出现。在当时,这大约标志着对一部书的认可表态吧。
笔者阅读有关钱锺书的相关资料时感觉,他与夏承焘的这节交谊,人们涉及较为有限。从后来的文章中我们知道,对《宋诗选注》这部潜心数年完成的著述,钱锺书是颇为看重的。可刚出版就被一通批判,由通常心态猜测,应该很“不舒服”才是。在听到研究大家夏承焘对该书认可的话后,钱锺书心情可想而知。所以他给夏承焘寄诗表达感怀,再寄《宋诗选注》以示郑重,甚至寄上夫人杨绛译作……那一代文化人,情绪表达,通常含蓄内敛。这些连续作为,可以较为充分见出钱锺书此时的感念心情。这种表达,在钱锺书,并不多见。文人之间,有时对生活中的推杯换盏也许不甚看重。文字间的认同,却可以大大加深情谊。从夏承焘与钱锺书这段非常时期的文章“援手”情形,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中彼此间的感怀。这种心情,应当久久不忘。据笔者有限的阅览,即使后来的动荡岁月中,夏承焘到了北京后,也还专程去看望过钱锺书。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1975年8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下午偕夏癯老(夏承焘常以“癯禅”自属)夫妇去北京市文物组,看琉璃河新出土西周铜器,又至故宫参观出土文物,最后访钱锺书(现仍住在学部)。”日记简略,没有他们之间谈话情景记述,可惜。不过,在生命历程中,以学术立身的学人,有文字交集、结谊,足矣。
(本文原载《北京晚报》2021年2月10日,原题为《夏承焘与钱锺书〈宋诗选注〉援手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