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立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2015年5月20日
中国人民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经历了浴血奋战和前赴后继的英勇牺牲,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援下,终于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在那同仇敌忾的岁月里,舆论宣传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战地鼓动、激励我方士气的不可缺少的利器,宣传自由中国、争取国际同情和援助的有效方策。但在卷秩浩繁的抗战时期档案资料中,有一类珍稀文献似尚未被注意到,这就是专门为来华盟军和友人编印的关于中国资讯的英文宣传册。笔者最近有幸发现了这批宣传册,深感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现撰文试对这批文献进行简要的历史考察和内容梳理,特别对先父王佐良教授所著Trends in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以下简称《趋向》)这本专册进行研究探讨,并以最新发现的另外四十多篇他的早期著作为补充参考,概述文献的内容提要及其历史意义,阐释其思想发展脉络、文学方法源流以及风格特点。
近年来学术界在关于王佐良先生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大都侧重于他在建国以后的英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成就。现本文根据新材料、新方法、新视角,对王佐良早年作为进步文学青年的文学创作实践、他在民族危亡时刻所体现出的爱国热血青年的精神情操和他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对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和比较文学研究、跨文化研究等做出的重要贡献,提出一些初步的见解和思考,试图弥补这些方面研究的空白,更旨在抛砖引玉,为学界提供最新的资讯和线索以便进一步深入研究。拙文《文献勾沉——王佐良〈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与抗战英文宣传册》、该册的英文辑校文本和中译全文(王立译,杨国斌校)即将发表。本文根据《文献勾沉》节选了一些相关的资讯和论述,欣与读者分享。限于水平和时间,疏漏不当之处,敬希识家指正。
一
去年9月里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笔者在网上搜索浏览时,惊喜地发现了父亲王佐良先生的一篇珍贵的英文旧作。这是一部题为Trends in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的英文专册,著者是Wang Tso-Liang(王佐良)。手捧着这本外表粗糙而内容精卓的简朴文册,我心情十分激动。那些发黄的旧纸上似乎依然能闻到当年弥漫的战火硝烟。在历史的浪潮淘涌过后,这份几乎被湮埋的抗战文献竟然神奇地飘到了我的手边,不能不说是一种天赐的机缘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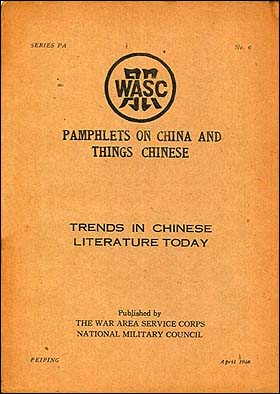
《今日中国文学之趋向》书影
这是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War Area Service Corps,Nation?al Military Council)战地服务团(War Area Service Corps)的英文宣传册“Pamphlets on China and Things Chinese”(《中国与中国的事物》)系列之一种。该册共28页。封面上方有战地服务团英文名缩写WASC和中文“服”字组合而成的圆形标识,出版地北平,出版时间1946年4月等。在正文第26页原编者注释中特别说明:本册的稿件写于抗战结束之前,大约1943年左右。
在封二有对出版这个系列的缘起和变更的简要说明。在封三有文字说明该系列是由军委会战地服务团为那些对“中国和中国的事物”感兴趣的人士所提供的“无倾向性的、可靠的资讯”。该系列按内容的性质分为三类:PA是关于学术兴趣方面的;PB是关于文化教育方面的;PC是关于普通兴趣方面的。抗战期间,这些小册子因为是战时通俗宣传品,不免成文仓促,编辑时有疏漏、舛误之处,且纸质粗糙、印制工艺欠佳,但反映了战时的实际状况。由于这类读物的性质和发行的特点,尽管当时的印数可能不少,但保存流传下来的却寥寥无几,愈显见其珍稀。特别是PA学术系列,涉及历史、哲学、新闻、经济(税务)、文学等方面,作者大都是这些领域的知名学者。如Gladys M.Yang(戴乃迭)著《马嘎尔尼爵士使华》(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及同册V.S.Phen著《图理琛访欧之使命,1712—1715》(Too Li Shin’s Mis?sion to Europe,1712-1715);金岳霖、冯友兰、萧公权合著《中国哲学与哲学家》(China’s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ers);孙瑞芹著《中国现代新闻》(The Modern Chinese Press)等。父亲王佐良撰写这篇《趋向》时只有二十七八岁,是西南联大(清华)外文系的青年教师。能独当一面地担纲概论现代中国文学的专题,可见他当时不仅英文出类拔萃,而且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虽然对于他后来撰写的近四十部著作来说,这只是一个宣传册,父亲生前也从未提到过它,但岁月沧桑、时代风雨难掩其精品佳篇的光彩。
二
先父王佐良1916年2月12日生于浙江省上虞县百官镇(今属绍兴市),自幼随父母在武汉生活。他先在汉口上宁波小学,从1929年起就读于英美圣公会等办的武昌文华中学,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他从小就喜欢文学,早年读过鲁迅、郭沫若的著作,并热爱古典诗词随笔小品等,担任过《文华校刊》主编,还经常写散文和诗歌,并开始接触英美文学作品,成了一个“文学少年”。最近笔者有幸查阅到了他在叶圣陶先生主编的进步文学刊物《中学生》杂志用笔名“竹衍”发表的短篇小说、地方印象记、散文等共八篇,时间在1934—1937年之间。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他对社会人生的积极探索,而且倾注着对国家河山沦陷、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当看到停产的汉阳铁厂和长江中游弋的船坚炮利的外国海军时,他愤懑于国家贫弱无国防的耻辱,对现代化强国的殷殷期盼也跃然纸上。在求学北上古都的列车上,更添怀古之情、兴亡之叹,他写下了面对强寇即将南侵的时局的慷慨悲歌般的感兴——
邯郸、望都……一个个古老的城镇过去了。我不能不想到古昔的历史。蒙恬、卫青的大军,他们都曾把足迹印在这平原吗?我想见往古如火如荼的军容,勇士们廓清漠北万里的雄心,以及那高大的白马,那些在北风里疾卷的大旗!如今呢,长城也挡不住胡沙了,光荣的远古的历史反令我们惭愧起来。(竹衍:《旅途》,《中学生》第59期[1935年],第167-170页)
当这位“南方的少年”到达“三朝畿辅”的文化古城后,他的心灵进一步为历史与现实的悬殊落差、传统与现代的剧烈冲突所震撼。在《北平散记》里他尖锐地批评那些“沉醉在过去的迷恋里,守住积满尘灰的古董”的文化守旧派:
古老并不是荣耀,印度埃及的故事早就是教训了,唯有自强不息永远的青春才是最可贵的。
有一天北平的人不再看着夕阳的宫殿而怀古,不再幽灵似地喊着“文化、文化”,而人人看向前面,朝初升的阳光挺起胸,跨着大步走去的时候,古城还有一点希望。(竹衍:《地方印象记:北平散记》,《中学生文艺季刊》第2卷第2期[1936年],第9页)
这种爱国热情尤其在父亲以笔名竹衍发表的《一二九运动记》中爆发了。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篇纪实地报道那场抗日救亡运动的文章,当年出自父亲这样一位温文尔雅的学人之手。他和一大批爱国热血青年学子一道,投入到游行示威的洪流中。文章首先概述了游行的过程,有不少细节再现了当时的情景。面对军警的野蛮镇压,学生游行队伍“千余颗心结成了一块铁”,“四人一排,整齐得像军队。他们挺着胸,步伐大大地,迈步前进。”(竹衍:《一二九运动记》,《中学生》第62期[1936年],第138页)文中还详细列举了运动的口号,并引用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包括那句有名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紧接着又批驳了对学生爱国运动的种种非议,揭露了为政府当局辩护的大学校方高层名流一类人的虚伪面目。最后,文章满怀激情地宣示了运动的发展和影响:
山山海海的呼声响应起来了,北平的学生是不会寂寞的。在上海,在天津,在武汉,广州、保定、太原、邕宁、宣化、杭州,在中国的每一角落,千千万万的学生都起来了,浪潮似的怒吼充满了整个中国。

1936年,王佐良在清华大学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父亲也开始流亡生活,随校南迁,先到湖南长沙、南岳,辗转至云南蒙自、昆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西南联大,一时间硕学鸿儒,精英才俊云集,汇聚起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群师生。据父亲的同窗挚友、著名英语教育家李赋宁教授回忆,当年他们考进清华外文系时,王佐良无论中、英文都是班上之冠。他读书非常勤奋,对文史哲各科都尽力涉猎,出色的英文写作几乎每次考试都是全班最好,曾受到贺麟、王文显、陈福田、叶公超、吴宓、刘崇鈜、钱锺书等各学科名师的交口称赞。在大学二年级举行的全校英语演说比赛中,他以《十年后之清华》(“Tsinghua Ten Years After”)为题目获得了第一名。清华校刊上以《英语演说比赛王佐良独占鳌头》为题作了详细报道。他在讲演中预言“中国收复失地,北平繁荣,清华扩大,设备更充实,研究风气大盛”,对未来的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十年后父亲的前瞻性豪言真的应验了,1946年夏他带着家人随校复员从昆明返回了久别的光复后的北平清华园。
在西南联大教授“当代英诗”课的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是一位英国现代派诗人、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在他的影响下,父亲对英国诗歌和诗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9年,父亲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学问上更是如虎添翼,非常勤奋地投入研究,“怀有强烈的学术和文化救国的思想”。他和青年历史学家丁则良先生在联大发起成立了“人文科学研究会”,定期举行文史哲学术讲座和讨论会,受到师生们的欢迎和好评。
在西南联大留校任教这段时间,王佐良的文学兴趣主要是研究、翻译英文诗,有时也写诗创作。闻一多先生曾把他的两首诗选入《现代诗钞》。后来的《西南联大现代诗钞》还收入联大诗人24家创作于1937—1948年间的诗作300余首,其中有王佐良的19首,今人多有传诵。笔者还发现他译成英文的自己写的3首诗歌,1946年发表在英国《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杂志上,但中文原诗还有待查考。该杂志同一期还有后来的《一个中国新诗人》的英文版:“A Chinese Poet”。母亲徐序亲自誊抄的父亲诗集遗稿共64首中,可能有32首未发表过,绝大多数为1979年至1990年间的新作。西南联大现代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杜运燮先生在《怀念诗人王佐良》一文中说:“我总觉得,他气质上是个诗人。”“他一生爱诗,写诗,研究诗,写诗论,译诗,编诗选。”多年勤奋耕耘积淀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大量的诗歌翻译实践极好地体现了他本人提出的“以诗译诗,诗人译诗”的主张。不仅是诗作,他写作的散文、游记、书评乃至学术论文都具有清新隽永的风格和富于神韵的文采。实乃文如其人,诗如其人。因此王佐良先生被誉为当代中国“一位不可多得的‘文艺复兴式’人物”。不久前,他的散文《浙江的感兴》被选为“2013年全国高考语文(北京市卷)”题目。最近笔者还发现这一时期发表的署名王佐良的14篇作品,笔名“佐良”的22篇,笔名“行朗”的一篇,加上前述用笔名“竹衍”的8篇,合计至少45篇,还有几篇待考证。如果我们把新发现的王佐良的诗歌和早期文学创作一并重新审视,也许会对他的文学成就和贡献有新的认识和更全面、更深入的评价。

1949年,王佐良在英国牛津大学Merton学院
还有几篇是中外文学评论。《波特莱的诗》对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今译名,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及其代表作《恶之花》(Lesfleursdumal)做了精辟的分析评论。《论法国作家圣·狄瑞披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介绍了法国作家、飞行员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今译名,1900—1944)的小说。文中分析论述了这位“现代法国最惊人的作家”的作品中人文主义的深刻内涵和影响。年轻学者王佐良不仅对英美文学有相当的造诣,而且对法国文学研究也有浓厚的兴趣。1947年秋,父亲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庚款公费留英,1949年在牛津大学茂登学院(Mer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获B.Litt. (Oxon)学位(1985年他收到牛津大学重新颁发的Master of Letters(文学研究硕士)的学位证书)。1975年他的学位论文《约翰·韦伯斯特的文学声誉》(The Literary Reputation of John Webster to 1830),由奥地利萨尔斯堡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结束了牛津研修以后,父亲毅然放弃了去法国继续研究的机会,于1949年9月回到北平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近四十年后,他应邀重访英法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研究,记述于《学府、园林与社会之间——英法两月见闻》一文中,可以说重温了他当年对研究法兰西文学的向往。
三
西南大后方虽然能有相对平静的读书环境,但战时物资匮乏,通货膨胀,生活拮据。为了养家,父亲四处奔波。据他在一首送给母亲的长诗中回忆,在繁忙的教学之余,最多时兼职打六份工。我们听他讲过的兼职包括在昆明的电影院给外国新片做同声口译等,到处跑场,疲于奔命,顾不上好好吃饭,落下了胃病。记得母亲也说过当时一家人喝白开水躺在床上等父亲拿回钱来买米下锅的情景。在《大学教育变质》一文中,他叙述了战时迁校的巨大变故,以及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在日寇飞机的轰炸下,各大学的师生们坚韧不拔,发愤图强,全力办好中国教育的精神风貌。最后他深情地说:
因为辗转流亡,一般的水准是降低了,然而在教学的认真和读书空气的浓厚上,却较以前任何时期而无愧色。在菜油灯下苦读,忍受着一切的不便而无怨言。甚至于藉课余挑水去换得一点零钱:这是中国青年新的面貌,温暖了多少心,又催下了几多感动的眼泪!读书已不是享受:这就是中国教育的变质。
父亲这时期还写了几篇散文游记描述了西南地区的路途印象,如《重庆初旅》《云南·贵州·四川》《一个典型的小县》等。在《受难的昆明》中,他描绘了这座在“自由中国”之内最美丽的城市,和它那富饶的物产、闲适的居家生活和幽雅的读书环境:
它面对着一个大湖,围绕在如带的长林之中,又与四郊的古刹大寺息息相通。高原气候使这里的树木长青,五谷丰盛,又给云南的居民以长年的阳光和脱了底似的蓝天。说风景宛如江南是不够的,因为江南没有这样明丽的色彩。一切都是那样清楚,人走在迷人的彩画之中,饮下了清晨的鲜明,回头来又化入了变幻的黄昏。晚饭后翠湖的小步是多么恬静的经验,也只有昆明才能给人这样与街市不分无门无窗的公园。
然而这一切美丽的和平生活被罪恶的战争所毁灭了:
但在那样的时候,警报响了。和平的人民逃出家屋,走入山谷和树林,平静失去了,生活成了一根张得太急的弦。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摧毁了昆明的风度,这是一个民族的罪恶,将在战争中得到清算的!
在这种艰苦条件下,西南联大等大专师生中有很多人参加了为抗战服务的各种活动,包括为援华盟军提供翻译、技术服务,乃至直接从军。父亲也用其精湛的外语知识积极参加抗战军援工作。在1941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时评,包括《德义的宣传技术:说宣传之一》《日本的谣言攻势:说宣传之二》《民主国家的反扫荡:说宣传之三》《论德军之渡海攻英》《租借法案通过后的新局勢》《一九四一年颂》等。这些评论观点鲜明,论证有力,准确地评估了当时复杂的国际时局,及时分析了各大战场形势,揭露了德意日法西斯的卑劣的宣传伎俩,显示了对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充满必胜的信心。在《论东西新闻体裁:为中国新闻学会成立写给报界》一文中,他以西方新闻的成功经验为借鉴,指出了写作战时报道的一些弊端,陈腐的套话、刻板公式化的倾向,提出了如何把新闻写得既短小精悍、具有风格特色又生动形象的建议。这些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观察可以说又为他后来的英语文体学和风格研究打下了基础。和当时大批知识分子一样,父亲努力为抗战做出自己的贡献的爱国热忱令人难忘。
然而这些在山河破碎、民族危难时一个爱国热血青年的所作所为却成了父亲及我们家人后来灾祸的滥觞。“文革”时他不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还被诬称为“洋三家村”而遭到抄家批斗,更因为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而长期饱受磨难,还被下放到湖北沙洋农场劳动了两年。最近家中发现了一本封面上印有“老三篇”图案的“工作笔记”,上题“王佐良《菜园记事》1971”。小本内记录了他从1971年5月至9月在农场菜园劳动时每日的活动、工作内容、瓜菜品种数量、收支分配记录等,清清楚楚,一丝不苟;还抄录了《中国蔬菜栽培学》上的各种瓜菜的英文词汇,以及“瓜类注意事项”等笔记。仅从这个小小记事本就可以看出父亲坚忍和达观的精神品格。不管在什么困苦逆境中,他都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和良知,勤奋忘我,自强不息,因为他心中一直有希望的阳光。
当“文革”的十年恶梦过后,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春天里,诗人王佐良重新拿起笔,写下了一首《城里有花了》来吐露心声。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在描述了“吹起了凄厉的西北风,从此沙漠爬上人们的心胸”的岁月里的惶恐和沉默之后,诗的后半部分是这样写的:
早已有了哥白尼,
早已有了加利略,
早已有了爱因斯坦,
早已有了几百年的星移斗转,
难道就是为了这样的终点?
不,人们说不,
人们说不是为这个,
人们开始只对自己说,
人们终于向大地吐露,
而人们是时间的宠儿。
草呀草,
绿又绿,
水边有树了,
城里有花了。
(1979)
由此可见,王佐良在这个英文宣传册中涌动的丰沛文思,来自清华—西南联大的高才学子的心声,文学青年的创作灵感,学贯中西的文艺知识,熟练精湛的英文功底,才华出众的诗人悟性,发自内心的爱国情怀,以及对中西跨文化交流的敏感和对人生命运的关注和悲悯……也许正是这种种不凡的资质,使得父亲成为向世界人民宣说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位特使。下篇我们将看到,他如何文思才涌、行诸笔端、游刃有余地写就了这一几乎被埋没的卓然奇篇,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战时向盟军和国际友人宣传中国的任务,还留下独具特色、动人心弦的文采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