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
本文要点
从学术训练和治学方法来看,与其说潘光旦是位社会学家,不如说他是社会生物学家(sociobiologist)。潘光旦的系列研究虽然取材多样,视角总不出社会生物学的范畴——除了他晚年的民族研究。
在社会学天地里,潘光旦就像一位居住在他国的孤独移民,既不愿融入当地文化,还宣扬着母国文化的优越性。囿于社会学的学科边界,我们便只能将他看作这一领域的“另类人物”,或所谓“生物学派”的代表。无论民国末年的院士选举还是今天的专业研究,都在学科的藩篱下低估了潘光旦的学术贡献。
潘光旦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曾提出“清华四哲”之说,除了陈寅恪、叶企孙和梅贻琦,剩下一位就是潘光旦了。其中陈寅恪是历史学家,叶企孙是物理学家,梅贻琦则是教育家。至于潘光旦,有人说他是社会学家,因为他当过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有人说他是心理学家,因为他翻译过霭理士的名著《性心理学》;还有人说他是民族学家,因为他晚年做出了几项开创性的民族学研究。其实,潘光旦自我定位首先是一位优生学家,其他的“家”都是派生出来的。今天我们从长时段的学术史脉络里更宜将他尊为中国第一位社会生物学家。这并非笔者标新立异,只有如此才可以将潘光旦的学术训练、学术思想和学术命运统合起来,进行更有解释力的阐述。
01 从生物学训练到开创社会生物学研究
1922年秋到1926年秋,潘光旦在美国留学四年,连续攻读本科和硕士学位,并主动放弃了博士学位。其间他曾在四所机构学习:达特默思学院、纽约冷泉港实验所、哥伦比亚大学和马萨诸塞州的海滨生物研究所,所学的内容均与生物学有关。他当年在哥大师从遗传学家摩尔根,后者曾获得1933年度的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属于当时生物学界的领军人物。按常理来说,潘光旦只要追随摩尔根的研究方向,回国推动遗传学的学科建设,就能成为中国现代生物学开创者,在谈家桢之前成为“中国的摩尔根”。

1924年潘光旦在美国达特默斯学院
然而,潘光旦治学的落脚点在人类,而不在动物。在当时的西方学界,优生学是生物学的应用学科,它以人类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并结合了社会科学和历史资料,最能满足潘光旦的学术兴趣。冷泉港的优生学纪录馆(Eugenics Record Office)是美国优生学的研究重镇。潘光旦在那里系统地接受了优生学培训,这决定了他此后的学术道路。在留美的短短四年中,他在优生学纪录馆的学习时间长达一年半,并与该馆主任达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1923年11月,来美仅15个月后,潘光旦就发表了题为《优生学与中国(Eugenics and China)》的英文论文。
优生学吸引了清末民初的不少中国思想家,包括谭嗣同、康有为和章太炎等人,他们提出过种种优生方案,可潘光旦普及优生学的功绩无人可及。优生学的要旨在于将人类的品性分为不同等级,通过生育技术和公共政策控制人类的演化进程,让“品性良好”的社会成员提高生育率,也让“品性不佳”的社会成员降低生育率,潘光旦分别称为“留强”和“汰弱”的优生学。作为一门应用科学,优生学的理论基础在于社会生物学,西方当时的很多优生学者同时也是社会生物学家。潘光旦的学术贡献更多在于阐明理论,而不是研究优生政策,因此他更宜被视为社会生物学家。
所谓社会生物学,即用生物学理论研究社会现象,或用潘光旦的话来说:“站在生物学的立脚点来观察文化。”潘光旦的中文著作多用“人文生物学”一词,含义相近。只是今天的社会生物学研究所有社会性动物(如蚂蚁),潘光旦的关注点更在于人类自身。从学术训练和治学方法来看,与其说潘光旦是位社会学家,不如说他是社会生物学家(sociobiologist)。潘光旦的系列研究虽然取材多样,视角总不出社会生物学的范畴——除了他晚年的民族研究。
早在留学美国时,潘光旦就用“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ical)”一词来形容自己的研究范式,他在后来的中文译本中明确写道:“……绳以今日社会生物学之学理,则可知孔门学识独到之处,有足惊人者。”他还列出了儒家学说和社会生物学的对应关系,说明两者多有相通之处。据生物学史家研究,动物行为学家斯各特(John Paul Scott)在上世纪40年代末的一次生物学会议上首次提出社会生物学一词,潘光旦比他还早二十多年。
在社会生物学家看来,就像其他动物一样,人类行为至少部分由自然选择所形成的遗传因素决定。这里仅举三例,说明潘光旦的社会生物学视角。他曾根据一些生物学者的观察指出,就人类品性的变异程度而言,男性一般稍大于女性,这也许是女性天才较少的部分原因。这一解释显然不同于强调环境因素的社会学解释。有些当代研究肯定了这一观点,虽然尚不能得出一致结论。
潘光旦还指出过农业社会中父母包办婚姻的进化优势——“彼(父母)以其比较丰富之经验,比较冷静之态度,必有以补子女之不及而匡正其失。”正是在相近思想的基础上,希腊生物学家阿波斯泰娄(Menelaos Apostolou)于2017年提出了复杂的婚配演化模型。
在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优生原理》中,潘光旦还提到过欧亚大陆与美洲的人类具有不同的进化史,抵抗病菌的免疫力相差很大,因此印第安人在欧洲人登陆后大量死亡。美国地理学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上世纪90年代末出版《枪炮、病菌与钢铁》后,这一观点才在学术界普及开来。
02 社会生物学家潘光旦的主要贡献
作为中国第一位社会生物学家,潘光旦的主要贡献在于介绍和发展了社会选择论。在他看来,人类演化除了由自然选择决定,还受社会选择的影响。社会选择是指观念、风俗和制度对人类生物演化的作用,它虽不能改变遗传的机制,却可以左右选择的方向。在1925年发表的《近代种族主义史略》中,潘光旦概括了社会选择的标准:“文化势力之善者与天择并行不悖,可使人类日益精进;否则倒行逆施,可使强亡弱存,优败劣胜,陷种族于危亡之域。此派学说(社会选择论)之正宗,其后演为优生哲学……”这里潘光旦明确指出,社会选择论是优生学的前导学科。
那么,哪些社会选择有利优生,哪些不利呢?就一个社会内部而言,潘光旦主要看重有利于其“优秀分子”婚配和繁育的制度和观念。他相信“文化盛衰由于人才消长,而人才消长由于生物原因”,社会选择通过影响人才多寡,间接地决定着一国文化事业的繁荣或衰退。潘光旦虽然承认个人成就受到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即生物遗传、文化遗业和平生遭际,他仍认为生物因素“最为基本”,另外两者属于次要的外因。“真正的人才,第一靠遗传的良好。但他可以成才到什么程度,局部也要看他所处的社会有多少文化遗业,有什么文化遗业。”
潘光旦对民族兴衰的解释与此类似,在生物遗传、地理环境和文化遗业三个因素中,“遗传最为基本,其次是环境,又其次是文化”。这种观点多少得到了美国生物学家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的认可:“文化并不是通过基因得以传承的,……然而,不能忘记的是这种作用因素(文化)完全依赖于人的基因型。”当代社会生物学的集大成者威尔逊(Edward Wilson)也指出,很多个体品性都具有中等程度的遗传率,群体间的遗传差异可能造成了社会之间的文化差距。
潘光旦的遗传决定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优生学的创始人,英国科学家高尔顿影响。高尔顿首先使用进化论原理和家谱材料解释历史上的天才现象,他相信“……通过连续几代人审慎的婚配,产生一批天赋很高的人才,这是相当可行的”。像高尔顿一样,潘光旦认为社会选择论之于中国的意义,在于“如何利用已然的现存的文化势力,和如何产生新的文化势力,使中华民族里比较优秀的分子可以取得婚姻生产的保障,取得婚姻率生产率的提高”。他虽认为中国不乏聪明强干者,却也警告说:“一个不理会社会的生物基础的民族,一个但知利用生物本钱而不知自觉的与自动的来增加这种本钱的民族,是危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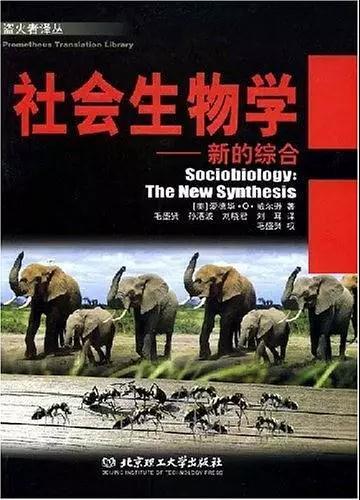
威尔逊(Edward Wilson)的名著《社会生物学》中译本
在增加“生物本钱”的意义上,潘光旦肯定了魏晋时代的选官制度,因为它保证了一种优生功能:“选举制施行后第一步的效果是定流品,流品越好,社会身份越高,婚姻选择的范围越狭,选择的标准越严;故家大族,流风余韵,因而可以历久不坠,民族有故家大族做领袖表率,也得以历久而不衰微灭亡。”他依此解释大书法家为何集中于这一时期:“……魏、晋、六朝、三唐书法的发达,是因缘于门地主义的婚姻;两晋比较的更发达,是因为门地讲得更严格,王卫二氏的特殊发达,是因为门地的讲究而外,再加上好几代的血缘结婚。”潘光旦对科举制度的辩护和批判也都基于社会选择论:由于科第选拔的原因,基因优秀的人才更容易彼此婚配,造成后代的“品貌整齐”。
英国思想家伯林曾将学者分为两类——刺猬和狐狸:“狐狸知道许多事,而刺猬知道一件大事。”潘光旦的学术兴趣广泛,似乎像个狐狸式的学者,他晚年也曾自嘲:“我这一生仍是博而不专……”其实,潘光旦的研究大都基于社会生物学,他真正是位刺猬型学者,符合伯林说的“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成条理明备的体系”。潘光旦按照存续优良血系的原则,审视历史上的制度和习俗,并给以生物学意义上的功能主义评判。我们应当从他知道的“一件大事”重新评价他的学术贡献。
03 面向单一学科还是整个学术界?
当代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的学者,常常将潘光旦列为名家之一。可潘光旦在民国时期只是接近了一流学者的地位。1948年,中央研究院举行过一次院士选举,潘氏属于社会学类候选人之一,最后选出的院士中并没有他,而陈达和陶孟和当选了。潘光旦与社会学的关系也是貌合神离,他自称:“……半路出家的我,根本对它(社会学)没有太多的情感上的联系。”除了孔德和勒普雷等少数几人,他很少正面引用西方社会学家的作品。潘氏同孙本文、陈达和吴景超等民国社会学家展开过激烈的学术争论,每次都站在强调生物因素的一方。
潘光旦在同代人的眼中没有进入一流学者之列,他对当代社会学的贡献也不显著。从论文引用量来看,他和费孝通对社会学研究的影响甚至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基于中文社会科学索引数据库(简称CSSCI),笔者搜索了标题中包含潘或费姓名的社会学论文篇数。从1998年到2018年,与费孝通相关的社会学论文高达87篇,与潘光旦相关的只有9篇。一位学者求学时未进入社会学专业,治学时不沿用社会学理论,其学术遗产对社会学界也没有很大影响,我们就很难高抬他在社会学史上的地位了。

左起:费孝通、孟吟、潘光旦、吴文藻
不过,某位学者对一门学科的贡献并能不代表他对整个学术界的贡献,我们将潘光旦的研究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来看更有意义。作为中国第一位优生学家,潘光旦回国后不可能找到美国冷泉港那样的研究机构,他也不能像老师达文波特那样获得大笔资助,因此他不得不在社会学界谋职。在社会学天地里,潘光旦就像一位居住在他国的孤独移民,既不愿融入当地文化,还宣扬着母国文化的优越性。囿于社会学的学科边界,我们便只能将他看作这一领域的“另类人物”,或所谓“生物学派”的代表。无论民国末年的院士选举还是今天的专业研究,都在学科的藩篱下低估了潘光旦的学术贡献。
作为中国最早的社会生物学家,潘光旦根据社会生物学的原理分析和评判中国历史,尤其是儒家的文化和制度,这当属于他最大的学术成绩。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今天已经集结成《儒家的社会思想》等书。他在中国开创了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范式,引进了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在这一领域走在国际学术界的前沿。在《优生原理》和《人文史观》的著述中,潘光旦的思考不仅涉及文化对人类演化的作用,文化自身的演化和选择过程,还探讨了文化与生物的协同演化,例如他对东西方宗教的社会生物学分析。当一本介绍社会生物学原理的著作《普罗米修斯之火》在1990年被译介到中国时,人们已经忘记了民国时期就有人将这把“火”盗回国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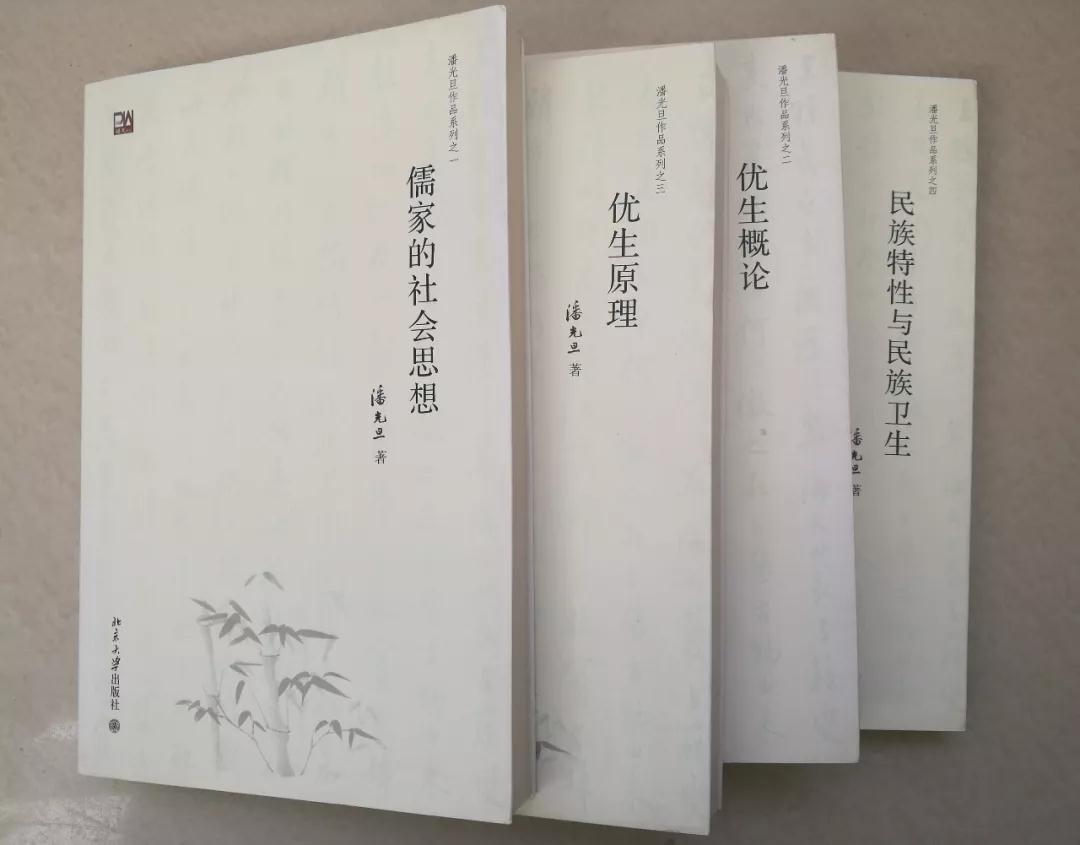
潘光旦部分著作《儒家的社会思想》《优生原理》等
在家谱学和天才研究方面,潘光旦结合史料,进行过大量开创性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学理和方法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后来的学者很少使用他整理过的材料,也不宜评价过高。在先天和后天的争论持续一个多世纪后,现在的学者至少清楚,高尔顿高估了先天因素,因为他并没有将先天和后天因素在统计上分开处理。潘光旦也跟随高尔顿犯了类似的错误。
今天,发达的行为基因学(behavior genetic studies)能够更清晰地揭示遗传现象。行为基因学家使用“遗传力(Heritability)”这一指标来测度生物因素的作用。成年人的智商在0.8以上,即基因差异可以解释成年人口中80%的智商差异。个性(如外向/内向)在0.5左右,偏好(如艺术/研究)仅在0.3至0.4之间。如果天才的产生仅仅取决于智商,那么遗传机制将起到主要的决定作用。但是他们不能仅仅依靠智商取得杰出成就,内在的个性和偏好,外在的机遇和条件,同样也很重要。而且,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很可能具有乘数效应,它们的相互作用还没有被研究透彻。可以想见,潘光旦当年对遗传和环境作用的理解就更缺乏严谨的科学依据了。他也曾承认这点:“就目前(上世纪40年代末)论,我们对于造成复杂品性的若干单纯品性,事实上还分辨不出,姑无论其背景里的种种基因了。”
尽管潘光旦过高估计了遗传因素的影响,对社会选择的理解也不像后世的社会生物学家那样顾及多个层面,但他对人类行为的生物学解释,依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留下了光辉的印迹。主流的社会学家一般偏向于使用环境论或文化论解释人类行为。潘光旦的一大贡献在于抗衡这些理论,与同时代的社会学家展开辩论,维持了思想生态的平衡。
虽然潘氏过于重视遗传因素,可并非不承认环境影响。在他看来,问题在于社会学家常常忽略生物因素:“……在文化社会学家方面,对于先天的种种能力或能性,却大有掉头不屑一顾的态度,坐使二派学问(先天派与后天派)彼此不能携手,互相启衅,这是我认为很不幸的。”上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生物学家拉姆斯登(Charles Lumsden)在书中再次强调了这点:“人们既不是由遗传决定的,也不是由文化决定的。它们是由某种介于二者之间更有趣的环境所决定的。”
二战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人的行为越来越被看作一种社会现象,而非生物现象。社会学家将生物学看作与己无关的“自然科学”,今天依然很少接触生物理论,甚至走向了后现代主义或极端相对主义,被英国学者狄肯斯(Peter Dickens)称为“过度的社会学化”。潘光旦早年的告诫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威尔逊就像他一样批评当代社会学:“在这种复杂性水平的人类社会研究中……它(社会学)企图基本上以最外部表现型的经验描述和孤立的直觉来解释人类行为,而不参考真实基因意义上的进化解释。”
二战以后,西方学界有关动物行为的研究突飞猛进,又推动了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上世纪70年代后,演化心理学和基因行为学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这些学科的成果如今已蔚为大观,我国也译介了数量众多的专著和科普读物。与此同时,生物科技日新月异,人类已经能够改变遗传机制本身,有关的技术和伦理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在新的时代精神下,潘光旦作为中国第一位社会生物学家,其学术思想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意义理应受到更高的评价,他开创的研究范式也值得后学继续发扬光大,以补充当前社会科学忽视人类生物性的不足之处。
(本文系为纪念潘光旦诞辰120周年而作,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本文转载于《中华读书报》微信公众号)